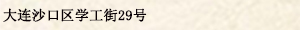论文汇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
本文从一个作物的视角展开,符合了时下颇为流行的“物”的历史的研究,反映美洲作物的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和变化驱动力。研究给予南瓜这类今天看来是单纯蔬菜作物以去边缘化的历史地位,以南瓜为中心,进行时间、空间视角的整合,阐述其多元化的历史功能和意义。笔者一向研究各类作物的历史,必然会涉及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及其规律,所以也就关联起了历史农业地理和社会经济史,是笔者的一个研究走向。期待与学友切磋。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的核心章节,博论拟以《中国南瓜史》为名出版。
作者:李昕升,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研究人员/经济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4期。
[摘要]南瓜原产于美洲,根据方志记载南瓜在16世纪初期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一带,作为菜粮兼用的作物迅速在全国推广。重点考证了南瓜在中国引种的时间、路径以及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中国的推广和分布情况,对南瓜推广的动因及其影响也进行了分析研究。
南瓜原产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常见别名有倭瓜、番瓜、金瓜、饭瓜等。南瓜是我国重要的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在我国已有余年的栽培历史。南瓜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在我国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多有种植,单产很高、产量颇丰。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瓜菜,还可作为饲料和中药材。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南瓜消费国和种植国,但对南瓜史的研究很少。有学者认为南瓜的起源和产地是多源性的,南瓜既有中国原产,也有国外引入;有学者阐述了南瓜的定义、南瓜的起源和印第安人对它的栽培、南瓜传入欧洲、以及南瓜传入中国,系统研究了世界南瓜史。但对于南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的研究却是空白。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明清民国方志记载为基础,着重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过程,并对南瓜在中国推广的动因、影响做出分析。
1南瓜引种的时间和路径目前我国最早对南瓜的记载见于元末贾铭《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又见于明初兰茂《滇南本草》:“南瓜,一名麦瓜,味甘平,性微寒……”。南瓜作为主要美洲作物,一般认为是在哥伦布年发现新大陆之后,同番薯、玉米等一起,随着欧洲向美洲探险、殖民、宗教传播的高潮进而在世界范围引种推广的。但是以上两部古籍均成书在此之前,疑是后人窜入。
我国现存史料没有南瓜在前哥伦布时代栽培的记载,目前也没有南瓜的野生种在中国被发现,说明南瓜确是从国外引入。根据方志等史料记载南瓜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间和路径是在16世纪初期的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一带。方志是研究明代以来南瓜在中国引种推广重要史料。笔者以方志为基础整理出表1。(排版原因,表略)
南瓜在中国引种推广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各省最早记载南瓜的时间多处于16世纪中后期,福建、广东、浙江、云南四省甚至在16世纪60年代之前,而福建最早在年。方志记载时间肯定会晚于实际的栽培时间,因此南瓜引种至我国的时间应该在16世纪初期。
在16世纪就记载的南瓜的省份共15个。在这15个省份中,东南沿海的省份是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在华北沿海,近海是安徽、江西,云南在西南边疆,河南、山西、四川、湖北、陕西、湖南在内陆地区。南瓜在福建与云南最早记载时间仅相差18年,如果南瓜仅由一条路线引种,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相距甚远的两地间推广并记载的,而且福建、云南之间相隔的众多省份最早记载时间均远远落后于两省。
南瓜引种到我国路径,根据方志记载可分为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东南海路,第二条路线是西南陆路,以第一条路线为主。东南海路,是南瓜首先传入东南亚,然后引种到我国东南沿海。西南陆路是南瓜传入印度、缅甸后,再进一步引种到我国西南边疆。
西南边疆地区南瓜最早见于兰茂(-)《滇南本草》的记载,成书之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该书在清初之前一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坊间流行,难免有后人托名兰茂增加内容。但本书现存最早的传抄本,汤溪范行准收藏的《滇南本草图说》十二卷,注明了是范洪在嘉靖丙辰年()根据《滇南本草》原著整理而成,其中已有对南瓜的记载,所以南瓜至迟在年已经在云南引种栽培,而且很有可能是从缅甸传入的,隆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均见南瓜记载。南瓜在云南向来有“缅瓜”之称,此称呼未见于它省,“南瓜,一名缅瓜”,“缅瓜,种出缅甸故名”。滇缅交流十分便利,滇缅间的通衢大道又称“蜀身毒道”,在云南段东起曲靖、昆明,中经大理,西越保山、腾冲、古永,可达缅甸、印度,《滇略》中描绘了滇缅大道的繁荣景象:“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缅甸也有栽培南瓜的记载,虽然没有缅甸明代栽培南瓜的记载,只有云南县知县周裕在乾隆32年()远征缅甸有记载:“其余食物,有冬瓜、南瓜……”。
东南沿海各省南瓜记载时间普遍较早。嘉靖17年()《福宁州志》载:“瓜,其种有冬瓜、黄瓜、西瓜、甜瓜、金瓜、丝瓜”,是我国对南瓜的最早记载,“金瓜”是南瓜常用别称之一,“江南人呼金瓜为南瓜”,今天在福建也多称“金瓜”。“金瓜”虽有时不指代南瓜但此处却是南瓜,乾隆《福宁府志》载:“金瓜,味甘,老则色红,形种不一”,根据性状描写确是南瓜,不只是乾隆《福宁府志》,历朝历代的《福宁府志》均未出现“南瓜”一词,事实上南瓜已经引种到福宁府(州)并以“金瓜”为代称,冯梦龙在崇祯10年()记载福宁州的寿宁县“瓜有丝瓜、黄瓜,惟南瓜最多,一名金瓜,亦名胡瓜,有赤黄两色”。浙江、广东也也很有可能从南洋引种的南瓜,浙北平原“南瓜,自南中来”;广州府、肇庆府是南瓜在广东的最早登陆地区,“南瓜如冬瓜不甚大,肉甚坚实,产于南中”,“南中”,比广东更南或是引种于南洋了,仅凭借此资料或许不能直接说明南瓜引种于东南亚,但是东南沿海各省对南瓜的记载均为全国最早,且明代的记载次数也为全国最多,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南沿海是南瓜的最早传入地区,也很难想象引种于东南海路以外的其他路线,而且多数美洲作物的最早登陆中国的地点也均是东南沿海一带。
南瓜首先被哥伦布及以后的航海家陆续发现并被引种到欧洲。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年征服马六甲,开始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作物开始传入南亚、东南亚。葡萄牙人从16世纪初开始便多次展开对华贸易,而且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往往能交易的物品都用来交易,南瓜可长时间贮存,适合参加远洋航行,所以南瓜可能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中国的广东、福建。“葡人海上进展如此的快,他们已引进到果阿(印度西岸港口)的美洲作物在印、缅、滇的传播照理不会太慢”。另外,中国与马六甲的交流在当时也很频繁,也可能由侨商直接从东南亚引种到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
2南瓜在中国的推广南瓜在方志等史料的最早记载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瓜在中国的引种路线。虽然仅凭记载时间的先后,不能反映南瓜在各省间具体的推广情况,但结合一些经济、社会因素进行合理性分析,能够反映南瓜在国内的推广的趋势。图1首先反映南瓜明代引种以来在全国的记载,南瓜在中国的推广情况即以这些方志为基础。
图1南瓜在明清、民国时期全国记载情况
南瓜在首先引种到福建之后就充分发挥了外来物种的优势,不逊于本土瓜类,从最初集中栽培的闽东北的福宁府和福州府,迅速推广到与广西、广东的交界的山地,如建阳县、归化县(今明溪县),但在明代用于供佛,不作为主要食品,以漳州为甚,“圆而有瓣漳人取以供佛,不登食品”。入清南瓜已经是“处处有之”,乾隆《福建通志》中已有十府记载南瓜。南瓜在台湾通称“金瓜”,康熙《诸罗县志》始有南瓜记载,未知是从福建引种还是从欧洲引入,但因福建移民台湾较多,从福建引种可能性更大,清初台湾南瓜栽培集中在西南平原,也是移民最先进入的地区,道光年间中部的彰化县开始记载南瓜,同治年间推广到西北部淡水厅(今新竹市),南瓜主要分布在台湾西部平原,东部山地栽培很少。
广东同样首先在沿海地区推广南瓜,广州府的新宁县(今台山县)、新会县(今江门市)分别在嘉靖24年()、万历27年()引种“金瓜”,而且名称一直沿用至光绪年间未出现“南瓜”一词,接壤的香山县(今中山市)载“金瓜,俗名番瓜,色黄”,乾隆《肇庆府志》载:“南瓜,又名金瓜”,都证明金瓜在两府指代南瓜。紧靠广州府的肇庆府内最北与广西的交界的封川县明代已见南瓜记载。南瓜在入清之前主要集中在广州府、肇庆府、高州府和雷州府。清代以来南瓜记载更加丰富,沿海各府均有,如潮州府康熙年间少见记载,但到乾隆年间已经“俗所谓南瓜潮产亦多”。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南瓜已经无县不种。南瓜在海南从康熙以来一直局限在北部近海平原,作为一般蔬菜“各属亦有之,惟出产不多,尚无输出”。
浙江在明代就记载南瓜达21次之多,广泛分布于浙东、浙西的平原山地各个州县,仅从方志记载地区来说,在明代东南沿海各省中推广范围最广。根据前文已引用的崇祯《乌程县志》,浙北平原应该直接引种于南洋,所以舟山岛南瓜在天启年间就被列入瓜属;浙南温州府与闽北的福宁府相邻,温州府南瓜有可能从南部的福宁府引种。在明末已经从沿海各府推广到与安徽、江西交界的开化县。康熙《东阳县志》载:“明万历末应募诸土兵从边关遗种还,结实胜土瓜,一本可得十余颗,遂徧种之,山乡尤盛,多者荐食外以之饲猪,若切而干之如蒸菜法可久贮御荒”,可见浙中南瓜可能引种于海疆,可御荒可饲猪,适合在多山的浙江广为种植,清初推广速度也很快,“郡县旧志俱不载,今邑中园野所在皆是,故补入”。南瓜在浙江引种之后,便通过京杭运河向江苏推广,所以宿迁县虽处苏北却较早引种(在江苏仅晚于丹阳县),运河沿岸的宝应县、江都县、沛县等地先后在万历年间栽种南瓜。明代除了京杭运河沿岸,太湖流域、长江下游南瓜栽培比较集中。入清之后南瓜栽培开始向苏北扩展,盱眙县、大丰县、东台县均见记载。总体来说南瓜在太湖流域最受青睐,“南瓜,此数种,几无家不种”。
江西明代栽培南瓜的地区主要位于赣西北一带,很可能引种于福建。因为明末赣西北的流民活动日渐明显,以闽省流民居多,到崇祯时达数十万人之多,并且活跃于赣西北山区的闽人主要来自闽南山区。清初南瓜栽培依然主要集中在赣西北一带,如康熙《南康府志》:“南瓜……四县皆出”。康熙年间赣东南的赣州府,随着客家流民接踵而至,南瓜也开始进一步推广。“南瓜,俗呼北瓜,又名番瓠,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处处有之”,反映江西从福建引种并逐渐完成推广的情况。湖南万历末年方引种南瓜,比江西晚20多年。谭其骧先生认为湖南人主要来自江西,移民湖南的江西人又以庐陵道、南昌府居多,而且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在明代“江西填湖广”的趋势下,先引种南瓜的赣北很可能将南瓜带到湘北的辰州府。明代湖南记载南瓜虽然栽培很少,但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推广,到康熙年间广泛分布湘东和湘南。乾隆年间长沙府成为重要产区,“南瓜,湘潭株洲产最多,俗又呼为北瓜”,湘西北晚清逐渐普及南瓜。安徽南瓜的最早引种地点是西北部的亳州,亳州可能从江苏引种,亳州在淮河沿岸,与运河在洪泽湖交汇,水系贯通;还有东南部的宁国府,是多路径引种,嘉庆《宁国府志》载:“饭瓜,即南瓜,宁国向无此种,明嘉靖中仙养心官浙之严州,归携种植之,味甘可代饭,今六邑俱有”,可见宁国府南瓜是官方从浙江严州引种。安徽在清初除了中部的六安州、庐州府和广德州的部分地区没有引种南瓜,其他十府已经遍种南瓜。清末以来种植范围有所缩小,集中在皖南地区。
山东明代共记载南瓜25次,为各省之最,绝大部分南瓜记载集中在京杭运河一带,运河沿岸几乎无县不种,明代运河漕运十分繁荣,事实上江苏最早引种南瓜的地区是丹阳和宿迁,同在运河沿线地区,尤其是宿迁,位于江苏西北邻近山东,引种时间却在江苏领先,山东很有可能是经运河引种。南瓜最早记载之一的青州府濒临渤海黄海两大海域,或从江浙一带经海路引种,但发展缓慢,整个鲁东在明代也只有几处沿海府县栽培南瓜,如福山县(今烟台市)、即墨县、沂州(今临沂市)。清初山东各地已经多有栽培,充分利用了丘陵山地,只有鲁东部分地区(莱州府、青州府)记载不多。河北引种南瓜主要是运河经山东至河北南部,《本草纲目》载:“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包括顺天府在内的河北南部尤其是运河沿岸、海河流域在明代已经广为种植。乾隆年间《红楼梦》多次记载“倭瓜”,可见南瓜在河北的流行程度。清中期以来南瓜向长城以北的河北地区推广,民国时期“张北、怀安、龙关、万全、康保、宣化、逐鹿、阳原、延庆、沽源、赤城均产”。从方志记载次数来看,几乎康熙以来的任何时期河北都领先全国。
东北地区的南瓜,多系关内的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闯关东”引入。辽宁引种的最早,在康熙16年()已见于记载,随着关内移民的增加,光宣年间大面积推广,“倭瓜,种出东洋,今为常蔬,种者甚多”,在辽宁全省俱有栽培。黑龙江与吉林在辽宁后相继引种,黑龙江为流人首先引种,“流人辟圃种菜,所产惟……王瓜、倭瓜”,早于吉林的原因是流人的长距离迁徙;吉林虽然在光绪年间才引种南瓜,但推广迅速,吉林、黑龙江的南瓜推广还是主要从二十世纪开始,到了民国南瓜在吉林已经“为普通食品,境内多种之”,主要沿松花江、辽河和长白山南麓栽种;南瓜在黑龙江也是“农家冬日之常食也”,在松嫩平原中部、东流松花江中游支流流域栽培比较集中。
云南的南瓜栽培分布是从与缅甸邻近的永昌府、大理府向东扩展,基本沿滇缅大道分布,也可反映南瓜引种于缅甸。在清初已经分布在云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成为通产。“农庄家无不广植者,每至冬间家有数十百颗堆积如山,以供一岁之需”、“番瓜如斛大,重至有数百斤者”可见南瓜在云南的栽培盛况,光绪之前,南瓜已经在云南推广完毕。贵州在万历末年就从云南引种了南瓜,但发展缓慢,乾隆之前仍局限在最初引种的黔东北一隅,乾隆年间在全省分散栽培,分布在乌江流域、珠江上游水系,清末民国时期,南瓜已在大部分地区栽培。广西在康熙之前尚无南瓜记载,最初记载南瓜地点在西部的泗城府西隆州(今隆林县),“西隆州僻在边徼,山壅瘴重,珍异之物绝无种类”,南瓜能够成为西隆州的“常物”很有可能从云南引种;东部的桂林府阳朔县则可能由广东引种,“种出交广,故名南瓜”。根据雍正、嘉庆两朝《广西通志》记载,桂林府、平乐府、柳州府,也就是广西东北部是南瓜主产区。广西东南部、西南部乾隆开始只有零星栽培,全省范围直到民国才普及。值得一提的是南瓜别称在广西最多,约有20余种。
四川在万历初年就记载了南瓜,引种时间早于周边除云南外的其他六省,很可能是引种于云南。这与何炳棣先生的研究不谋而合,何炳棣先生认为明朝重开茶马市是美洲作物向京师和中国内地输进的可能媒介之一,而茶马市南方的重点是在成都西南的雅安、荣经、汉源一带,或由云南土司向北京进贡,可能经过贵州北上(贵州即是从这条线路引种南瓜),也可能大体沿着现在的成昆铁路北上。明代记载南瓜的嘉定州(紧靠上述雅安三地)和营山县正好处在这两条路线的必经之路上。但是四川南瓜发展缓慢,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局限在嘉定州和营山县所在的顺庆府,重庆府有零星栽培。从乾隆年间开始四川南瓜种植异军突起,普及速度、栽培面积领先全国,广泛分布在北起北川县南至屏山县以东的川中、川东地区。南瓜虽较早从云南传入四川,但长期停滞,川东、川南大部分地区的南瓜引种是从东南一路随移民入川而推广,即“湖广填四川”,民国《绵竹县志》的记载也反映这一史实:“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移种入蜀”。到了嘉庆年间川西北高原都已经成为南瓜著名产地,“两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巨槖,围三四尺重一二百斤,每岁大宁巡边必携数枚去,每一枚辄用四人舁之”。
湖北最西北的郧阳府在万历初年就成为了南瓜产区,“南瓜,俱竹山、上津、竹溪、保康”。勋阳府是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秦巴山区腹地、汉江中游,云南土司向北京进贡的重要路线之一,从四川嘉陵江转汉水必经郧阳府,可直达南阳盆地,进而一路北上,故湖北南瓜可能引种自四川。但推广缓慢,直到康熙年间南瓜开始在北部汉水沿岸和南部长江沿岸广为种植,鄂南是通过长江之便从下游地区引种,因此才会在长江流域形成以汉阳府为中心的南瓜栽培带。事实上,湖北到处充斥着来自江西的移民,如武昌地区以南昌地区的移民为主。河南虽地处中原地区,但早在嘉靖43年()就记载了南瓜,时间在周边所有省份之前,邓州位于河南西南,豫鄂交界部,西通巴蜀,南控荆襄,邓州处南阳盆地,同样是云南土司向北京进贡的重要路线之一。南瓜引种后在明代发展较慢,清初推广很快,在河南各府都是常见作物。山西南瓜栽培始于隆庆初年,南部汾河谷地的襄陵县(今襄汾县),从河南引种可能性更大,与河北间有太行山相隔,引种难度较大,到万历年间已经自南向北纵贯江西,同一时间推广速度之快远超其他省份,明代记载21次,万历《山西通志》就将南瓜列为全省级别重要瓜类。清初除了晋北的宁武府和大同府南部,南瓜在山西的推广覆盖率极高,直到民国栽培范围才有所缩小。
西北地区的陕西,最北的延绥镇、西部的岐山县、东北的白水县均是在万历年间引种,三地距离较远,而且周边省份南瓜记载最早时间均早于陕西,因此陕西可能是从湖北、河南、山西多渠道引种,尤以山西可能性最大。南瓜在康熙以来各府均有栽培,不过主要是陕北和陕南发展,中部地区发展较慢。宁夏、甘肃、新疆分别在万历末年、康熙初年、乾隆中期始有南瓜记载,丝绸之路上的陕西岐山县万历19年()引种南瓜,甘肃、宁夏南瓜应是从陕西经丝绸之路引种,乾隆之后集中在河西走廊和陇东南部分,尤其是陇东南分布相对广泛。新疆是多路径引种南瓜,不只从甘肃引种。乾隆29年()抽调盛京地区的四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移驻新疆伊犁地区以加强该地防务,管兴才《西迁之歌》载:“带上故乡的南瓜种子吧,让它扎根在西疆的土地上……”,因此新疆的南瓜可能还引种于辽宁。另外,康熙51年()图理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行程过俄罗斯境,至萨拉托付时载:“贩卖有……王瓜、倭瓜”,那么乾隆36年()土尔扈特部东归有可能将南瓜引种到新疆,也不排除更早经丝绸之路从西亚引种到新疆的可能性。乾隆以来,南瓜先是在天山南路已经成为了普遍栽培的作物,后扩展到天山北麓和昆仑山北麓。青海以畜牧业为主,直到民国时期南瓜才“青海各县均产之”。内蒙古邻近陕西、山西的呼和浩特地区在咸丰9年()首先引种,但未向畜牧区深入推广。
南瓜在16世纪初期由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引种到中国,在明代就完成了大部分省份的引种工作,在引种到中国的美洲作物中南瓜可谓是急先锋,不仅完全领先于番茄、辣椒等蔬菜作物,甚至比玉米、番薯等粮食作物更早的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普及,就全国范围来看,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南瓜在全国的推广最终奠定了我国世界第一大南瓜生产国的地位。
3南瓜在中国推广的动因南瓜在16世纪上半期始有记载,在17世纪初期就几乎传遍了中国。南瓜的推广速度完全领先于其他美洲作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推广动因可分为两大类。
(一)自然原因南瓜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瓦维洛夫通过考察指出南瓜可能来自科迪列拉山脉东坡。那里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多样,在这种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南瓜生长强健、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性。南瓜根系强大,最深可达两米,在旱地或贫瘠的沙土地上也能正常发育,并获得较高产量;南瓜在15°C到35°C之间均可正常生长,同时属于短日照植物,对土质选择不严。所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均适宜南瓜栽培,无论是“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的云贵高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江南丘陵,还是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南瓜均可栽培,“农家多种之,最易生”,“少水可收,至春间亦可切条晒干致远”,“用不着许多工作,自己便能生长”。另外,南瓜“宜园圃宜篱边屋角”,在十边地、零星隙地、瘠薄地、院前屋后均可栽培;还可以充分利用山田,“山田隙地多种之”。南瓜“味甘适口”,符合国人口味,南瓜子富含脂肪,炒食香脆可口。南瓜易于保存,“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南瓜单产很高,一般亩产南瓜到千克,“一瓜有重至二三十斤者,俗呼为王瓜,盖瓜中最大者”。南瓜的这些生态、生理适应性是在我国推广的前提。
(二)社会原因1、粮食供应紧张,民生问题突出
明代后期以来我国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全国人口密度从顺治18年的4.93人/平方公里,到乾隆18年24.06人/平方公里,再到嘉庆17年67.57人/平方公里和咸丰元年80.69人/平方公里。嘉庆17年()全国人均耕地仅为2.19亩。美洲作物的传播为拓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救荒类作物尤受青睐。南瓜虽在引种之初被视为普通瓜菜,随着缺粮少食的现象时有发生,高产、耐旱、可长期保存的南瓜很自然的发挥了“代粮”作用,入清以来更是被称为“饭瓜”,“田家一饱之需,孰过于此”。通过对各省的比对可发现,人地矛盾越突出的省份,南瓜救荒作用就发挥的越早,如江浙人口密度长期以来在全国领先,因此在明末南瓜就用于救荒,“凶岁乡间无收,贫困或用以療饥,是宜弗绝其种”。即使是情况相对较好的直隶,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在同时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人均耕地占有量趋于减少,势必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于是民生状况出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因此“南瓜总名倭瓜,可为蔬并可饱贫人,以之代饭故俗曰饭瓜”。清末河南救荒书的集大成者《救荒简易书》十分推崇南瓜的救荒价值,“老而切煮食之,甚能代饭充饱”,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栽种和收获期,是“救荒权益之法也”。尤其在粮食紧缺的冬日,南瓜可起到“御冬”的效用,“土人家家旋割作长条,晒干用以御冬”。而且南瓜的花、茎、叶均可食用,“花可佐酱,茎去皮寸断,炒食颇嫩脆适口”。
2、经济利益的驱动
明清以来近城邑之地常存在园圃菜蔬与五谷争地的现象,无锡“不植五谷,而植圃蔬,惟城中隙地及附郭居者为多,其冬菜一熟,可抵禾嫁秋成之利”,而瓜类获利尤多,“瓜之利厚于种稻,瓜熟一利也,摘瓜而即种菜二利也,半年之中两获厚利,故武山之佃田者多种瓜”。南瓜是瓜类中的佼佼者,“可切条晒干,煮食味与瓠条相似,远近负贩土人因以为利”,“少者自用,业圃者售于村镇”,南瓜能“代粮”但价格又低于五谷,因此能够使栽培南瓜的农民获利,如果南瓜种植形成了规模,能产生规模效益,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种植南瓜的“业圃者”,所以“有鬻于市者”,“滇中所产甚大,与冬瓜相似,市上切片出售”。苏南太仓州从乾隆开始“番瓜,亦出塘岸,苏人大舸来贩之”,一直到民国仍是“南瓜,俗名番瓜,邑种最繁,苏人大艑贩载而去”,上海亦是如此记载。南瓜子因“子可煼食”是重要商品,清中期以来颇为流行,“郡产南瓜最多,尤多绝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子可炒食运售亦广”,金川还成了南瓜子的著名产区,“子白色佐茗酒,产金川者贵”。南瓜用途广泛,深加工可产生诸多经济效益,“瓜有金瓜,即南瓜,大金瓜特异种空地,八九月始熟,大如罂坛重数十觔,皮肉俱黄,煮食甜甚,或切片晒蒸数次放酒壅中,酒作金色味如饴”;南瓜“又可为粉”,“可澄粉”;“宜蔬宜餹片宜饲豕,嫩薹宜豆汁,子宜佐茗酒”。南瓜还被广泛用作饲料,促进了农村畜牧业的发展,“邑人多以饲豕,亦有销上海者”,“可饲蜂,可喂猪”,是“夏季养蜂植物”。南瓜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南瓜的进一步推广。
3、瓜类栽培技术的成熟与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南瓜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也体现在栽培技术简单的层面上,可以套用传统的瓜类栽培技术,迅速融入我国的瓜类生产体系。如咸丰《归绥识略》结合《齐民要术》大篇幅的介绍了甜瓜的栽培技术,在介绍南瓜时只是一句“种者极多,法与种甜瓜同”。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瓜”目同样较多引用《齐民要术》瓜类栽培技术,结尾指出“菜瓜、黄瓜、丝瓜、南瓜法皆同”。正是由于我国的瓜类栽培技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就趋于成熟,而瓜类栽培技术颇有共性,南瓜适应性又强,因此南瓜在能够在短期传遍中国,得益于我国传统瓜类栽培技术比较成熟,农民不需要专门掌握南瓜的栽培技术。
我国夏季蔬菜却相对较少,所以每到夏季,常出现“园枯”的现象。据《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统计,我国汉代栽培蔬菜只有21种,其中夏季蔬菜4种;魏晋《齐民要术》的记载增加到35种,夏季蔬菜只占7种。明代之前,我国夏季蔬菜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在“夏畦少蔬供”的条件下,适合在夏季栽培供应的茄果类蔬菜很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明清形成了以茄果瓜豆为主的夏季蔬菜结构,弥补了夏季蔬菜品种单一的缺陷,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南瓜在夏季蔬菜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南瓜在中国引种推广的影响(一)发挥了救荒作用,缓解了人地矛盾南瓜在凶年、饥岁充分发挥了救荒作用。“饥岁可以代粮,先慈劝人广种以救荒”。在粮食不足时南瓜即为正餐,“南瓜即番瓜,黄老者佳,米贵之时以为正餐,颇熬饥”。南瓜味佳,救荒方式多样,“蒸食味同番薯,既可代粮救荒,亦可和粉作饼饵。蜜渍充果食”。革命年代的“红米饭、南瓜汤”,新中国成立后的“瓜菜代”,南瓜功不可没。总之,南瓜是极普通,也极重要的蔬菜,是寒苦人家日日必食、不可少的蔬菜,实为寒家救济之品。具体来说:
西北地区。“南瓜,有圆长扁各形,农人藉为接口粮”;“倭瓜,其种来自倭国,大如盆,乡间家种数亩,供餐饱食可代粮粟”,南瓜作为粮食的替代品,以至于占地“数亩”,如此大规模的栽培对于一般栽培在园圃中的蔬菜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华北地区。南瓜代粮比例十分之高,“南瓜,俗名饭瓜,贫民多植隙地储以御冬,可省菽粟之半”;“农家比户种瓜,至秋红实离离有,以北瓜补粟之缺”,在“田蔬”条目下,而不是“山蔬”和“圃蔬”,反映出了南瓜(在山西又称北瓜)“补粟”的重要地位。
华中地区。作为常见的救荒作物,“凶年人资之为饭”,“南瓜最富,六七月间田家饱饫焉”,而且“花叶均可食,食花宜去其心与须,乡民恒取两花套为一卷其上瓣泡以开水盐渍之,署日以代干菜叶则和苋菜煮食之,南瓜味甜而腻可代饭可和肉作羹”。
东南地区,成书康熙年间的《湖录》就载“番瓜相传自番中来,贫家以之代饭,俗名饭瓜”;可充当山地粮食作物,“味甜而富于小粉质,可以充饥,乡人每种于山田中”;“为乡人佐食之品种者,十家而九”。
西南地区。南瓜“可煮可蒸,荒年救饥,可饲豕”、“民佐谷食”,所以“吾邑家家种之”,今农家多种之”,“夏秋间之南瓜担者负者不绝于涂尤其取之不尽者”。
东北地区。“倭瓜,有长圆形不一,民间切片晒干谓之倭瓜干”,晒干的主要作用就是储备粮食;南瓜可贮存时间长,可储存用于冬日食用,“藏之可为御冬旨蓄”,“立夏下种,白露后花落实成宜熟食,农家冬日之常食也”。
(二)增加了经济效益南瓜虽然与其他蔬菜相比并不昂贵,但因产量很高,收益比较可观。年之前关于南瓜的统计资料较少,但一些零星资料可窥见一斑。(排版原因,不附表格)
从民国奉天省的情况来看,南瓜栽培面积虽远不及黄瓜,但远超菜瓜、冬瓜,而且南瓜单产很高,亩产斤,领先其他瓜类及大部分蔬菜,所以综合效益较高。“此瓜初结如拳如碗时清松适口,圃人摘卖于市得值较多,群呼小瓜或呼嫩瓜。崽志皮坚肉黄时味尤甘,圃人多剖而卖之,群呼老瓜,世之研讨植物者皆谓老瓜能制糖,信乎其能制糖也。”除了说明获利较多外,也可见南瓜是制糖的重要原料,“每斤三四钱,或云可煎糖、可制火药,泰西人尝为之”。
此外,将南瓜深加工“可酿酒”,南瓜酒作为一种嗜好饮料能够取得深加工的利润;还可作为肥皂的原料,“近时之洋肥皂,其黄色者,即此瓜所制也”;以及制作酱豉,“嫩时色绿老则朱红,俗人晒干以制酱豉”,均能增加收入。南瓜子“可充果品”获利颇多,“北方饷客尚倭瓜子”,无论南北方南瓜子都是流行商品。至迟在道光年间“南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南瓜子是零食中的上品,“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宾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宾筵则必以陕西之瓜子为贵”,陕西瓜子“为贵”,可见南瓜子的流行程度;“子,市人腹买炒干作食物,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民国时期还专门报道不同品牌南瓜子的价格行情,“南瓜子价俏:日新本牌(53元),衡州莲(42元)……成昌开出南瓜子数十包,肉实饱满,价开十四元五角”。
(三)对农业种植制度的影响南瓜在传入中国不久就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作物种植结构,尤其是园艺作物种植结构,在园圃中南瓜占了相当的比例,挤占了本土园艺作物的生存空间,“南瓜、倭瓜等类,则农圃多种之”。南瓜虽然在我国大规模的种植,但与原有作物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农业种植制度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南瓜植株较大,栽培株行距大,常常套作其他蔬菜或粮食作物,增加了土地利用率。Cortesd等()在南瓜种植一个月后,套作花生、马铃薯、玉米三种作物,发现三种套作方式都比单种好,其中最好的组合是花生和南瓜。南瓜的前茬可安排根茬菠菜,或早熟春播叶菜如小油菜、小白菜、水萝卜、茼蒿、甘蓝等,后茬可接种大白菜、秋菠等。在城镇郊区可以分别与早春包菜、马铃薯、大蒜或葱头、矮生地豆、速生叶菜等蔬菜作物间作套种,在广大农村可与小麦、玉米和矮生豇豆等粮食蔬菜混合间作套种。
(四)在中医方面的影响清代以来,几乎所有本草类、医药类典籍都会记载南瓜,南瓜药用价值很高,为我国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李时珍认为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南瓜可以断烟瘾,“近时治鸦片瘾,用南瓜、白糖、烧酒煮服,可以断瘾云”,在近代鸦片流毒严重的西南、东南地区起了极佳的抑制作用,李圭在《鸦片事略》中专门阐述南瓜的具体应用。南瓜全身是宝,“南瓜蒂……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药中,大妙”,南瓜瓤“连子装入瓶内,愈久愈佳,凡遇汤火伤者,以此敷之,即定疼如神”;“南瓜根,专治一切火淋火症,行大肠气胀解烟毒;南瓜花,性凉,治咳嗽提音解毒又达痼疾”;南瓜藤“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清人鲍相璈在《验方新编》中共记载“眼珠伤损”等十二个南瓜为主药的方剂。
(五)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南瓜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中诞生了“南瓜精神”,映鉴着信心、信念之坚定,同时还代表了艰苦朴素的精神和不忘根本的精神。南瓜本身具有观赏价值,成为食雕文化的一部分,“未熟时土人每雕花草人物之形于其上,迨七夕中秋取以献月,亦古风也”。此外,南瓜在文学创作中深受文人爱戴,早在万历年间《西游记》第十回中就提到了“刘全以死进贡南瓜”的故事;《红楼梦》及其各种后传、续传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到南瓜;清末吴趼人在《情变》第一回中大篇幅的叙述了南瓜救荒的故事。近代民俗中流行着“食瓜祈子”,其中“上海则异是,所食为南瓜,且谓必须夫妇同食一瓜也”。在今天,随着西方节日文化的传入,南瓜灯日渐流行。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是我国毛南族的南瓜节,农历八月十五是广西侗族的南瓜节。
公告通知经过两年的不懈坚持,“明清史研究资讯”北京那家医院治白癜风最好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