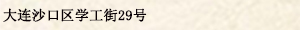他們有駱駝,而我們有剃鬚刀
他們都問起我來以色列的動機,或者說“使命”,我告訴他們我是讀了這個書,又讀了那個書,以色列的傳奇故事一直在撩撥我躁動的求知慾。
——雲也退《內奧·茨馬達紀事》刊登於《今天》年秋季號總第期
▎內奧·茨馬達紀事(四)
點擊標題閱讀前文:內奧·茨馬達紀事(一)、內奧·茨馬達紀事(二)、內奧·茨馬達紀事(三)
我從睡夢中醒來,農莊發的床單皺到一邊去了,沙漠空調轟轟地響個不停。孔雀開始淒厲地打鳴:咿嗷——咿嗷——拿起手機一看,中東時間早晨5:20。
第一次活着起這麼早。
可是馬克已經走了,他的床空在那裏,那把吉他靠牆扔着,表情很哀怨。
我是個時間觀念很差的人,女孩跟我第一次約會,就能懂得什麼叫天荒地老。昨天夏哈告訴過我,內奧.茨馬達的早集合時間是5點一刻,但這怎麼可能做到呢?五個小時前我剛剛關了電腦睡下,或者說,做出平躺的動作。我的腦垂體仍然處在興奮狀態。
興奮是因為剛剛看了一篇新聞。5月中旬,美國共和黨國會代表喬·皮茨寫了封信給一名議員,信中說:“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全球戰爭正在打響,當前,對阿里爾·沙龍總理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來說,鎮壓那些行暴力無度的巴勒斯坦極端主義者,讓業已破產的和平進程重新開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收信的這位議員名叫羅德威爾特,他的兒子伊安·羅德威爾特是個記者,任職於一家在中東地區發行、關心以巴衝突的新聞機構,於是他們家上下都很關切中東問題。老羅德威爾特剛剛寫信給白宮,表達他對白宮新通過的號決議的憤怒,因為這份議案支持解決以巴衝突並譴責巴勒斯坦人,收到這封答覆信後他冷靜了下來。他開始意識到,白宮裏拎不清的人比他估計的要多。
幾天之後,喬·皮茨先生收到了署名沙龍和阿拉法特的“公開復函”:
尊敬的皮茨議員閣下:
從耶路撒冷/聖城向您致意。
昨天,我們注意到在一封寫給一位議員的信中,您提到了我們的不作為是阿以和平進程失敗的原因……
首先,請允許我們聲明,聽聞您對和平進程產生的新的興趣,我們倍感振奮。請放心,我,阿里爾.沙龍,雖然處於植物人狀態,卻仍舊和阿拉法特主席——他目前定居在一口棺材裏——聯繫密切。我們已就實質性問題達成了諸多令人矚目的進展,但我們很難握手,因為我昏迷不醒而他已經死了。
請向您的總統羅奈爾得·雷根及副總統耶穌先生轉達我們對未來的樂觀態度。
鑒於美國政治家已對中東問題進展及最新情況瞭若指掌,合眾國能在我們地區的和平進程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不足為奇的。期待在您入主橢圓辦公廳之後不久,我們雙方就能簽下一紙和平協議。
此致
阿里爾·沙龍總理和亞西爾·阿拉法特主席
這樣的事情畢竟不常發生,所以,以色列人抓住機會狠狠地狂歡。他們知道兩件事:第一,他們要靠美國人,第二,美國人是靠不住的。相應的,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國是論壇裏大抵分為兩派,一派人愛問:美國人怎麼說?另一派人愛問:我們什麼時候能脫離美國了呀?像喬.皮茨這類稀裏糊塗的政客只是冰山一角。當然,以色列人可以指望華盛頓和紐約的那些猶太院外遊說集團,不過,他們也經常諷刺說,西半球的大老爺們要想表達對以色列的忠誠,最好的辦法就是舉着牌子到甘迺迪國際機場去迎接猶太背包客,讓他們用自己家的烘乾機烘襪子。
我披上襯衫出門。大夏天的清晨竟然還有一點微涼,讓人得意得直哆嗦。房門左邊站着一個長長的樹樁,這個村子的地形對我來說過於複雜,樹樁或許可以用作宿舍的標記。昨天晚上出門倒垃圾,我就認不得回來的路,這裏的一堆宿舍都長得差不多,更要命的是,都是用一模一樣的白條紋木板做的門,連一塊門牌都沒有。
農莊養着不少孔雀,這種鳥類平時昂首闊步,一聽到人的腳步聲立刻灰溜溜地亂竄。我抖擻精神往食堂走去,遠遠看見小廣場上坐着好些人。我徑直進食堂裏,只見有人進出卻無人落座,更沒有開飯的徵象,又出來,發現廣場上擺着張桌子,放着水、杯子和果醬。有人過來倒水,有人從廚房出來,拿着麵包來抹果醬,其他人都坐着,坐在草棚底下的,坐在水泥台階上的,直接坐在地磚上的,盤腿窩在草地上的。
一聲不吭。所有人都一聲不吭。
有的閉眼,有的半閉着眼,有的睜着眼,有的低頭,彷彿在研究螞蟻遷徙的路線。他們臉上有一種我在一幅名畫裏看見過的罕見的表情,要麼是波提切利,要麼是昂利·盧梭。他們都在做什麼呢?一個精力充沛的人肯定會傾向於同工作、市場、社會、電腦、運動、吵架、遊行或者性交打交道,這些事情是與他相配的,而一個精力充沛的人選擇安靜地坐着,很長時間一動不動,就一定有非常特別的緣故。
他們在冥想。我聽達尼埃爾說過這裏有冥想的習慣,就以為是像瑜伽房裏的那些人似的,把兩條腿掰成一左一右,把臉蛋埋下去,尾骨將健美褲戳得老高,保持這樣的姿勢好久好久。據我所知,二戰之後的西方人就在討論東方的瑜伽了,那個神經兮兮的匈牙利人亞瑟·庫斯勒,在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瑜伽修行者與政委》的隨筆集,他說,瑜伽修行者對藝術的追求是無力阻遏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的,無產者們忙忙碌碌,為的是解人民於倒懸,但是他們沒辦法把瑜伽修行分子們從倒立的睡眠狀態下喚醒。
我也找了一棵大樹下坐下來,很快進入了半睡狀態。我真的被昨天的工地活兒給累到了,即使上帝突然從旋風裏現形,我也只當是飛來一張舊報紙。人們總是到合適的地方去做合適的事情。人們去泰國享受推拿,去夏威夷曬日光浴,去印度參加靈修,去中國大快朵頤,去荷蘭嫖妓,去美國置房產;沒有人去印度曬日光浴,去泰國學農業,去中國買房子,去美國吃美食,去荷蘭靈修。我有很多通曉常識的朋友,他們要是聽說我在以色列參加冥想團體,肯定會緊張地問:“你後怕嗎?那兒的人是不是都徹底豁出去了?”他們認為以色列是個精英到牙齒的社會,精氣神跟戰前的第三帝國(呃,有點政治不正確了)有些相似,人人愛好運動,民氣旺盛,適齡的小伙子不太沉湎於女色,對女孩子綁在武裝帶裏面肉鼓鼓的身子看也不看一眼,全社會都沒有機會培養哪怕一丁點市儈習氣。
中國人,如果沒有生意場上的關係,一般不太能與以色列人有深入的接觸,他們是一些精密的機器,不停地轉動,在保家衛國的事業中準確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天,他們的巡邏隊伍經過哭牆下面,都要深情地敬禮,念一段經文,然後邁着整齊的步子走向約旦河邊的宿營點。“問題在於我們沒有宗教,”曾經有位資深的國際事務專家跟我說,“而他們要關心的事情遠遠比我們多,比我們大。我們開會的時候,開了一半他們要跑出去祈禱,而且從來不邀請我一起去。”
我完全不瞭解冥想,不知道它有什麼科學根據。我聽說,克里希納穆提在內奧·茨馬達是偶像,他的追隨者遍及全世界,他有那麼多的文字在流傳,或許猶太教裏有什麼理論能與靈修行為交融?我太無知了,需要學習更深的知識。我跟所有人坐在那裏,低下頭打盹,微風把我呼出去空氣又送了回來。快有近四五十人了,仍然沒有一點聲音,不斷地有人來,重複那個步驟,給自己拿麵包,抹果醬,沏上一杯水,手腳都輕輕的,然後隨便找個地方,屈下兩腿變成一棵植物。我們是一群寂寞又虔敬的沙漠修行者,我們與貝都因人的區別在於他們行走,我們靜坐,他們有駱駝,而我們有剃鬚刀。
我沒看清是誰第一個站了起來。總之,忽然之間,所有人就跟吸了符咒的紙片一樣活了起來。冥想時光結束了,變成了從休息向勞動過渡的一個中間狀態。人們開始各就各位。我的位置在哪裏?
食堂門口有一塊軟木佈告欄,那裏釘着一張工作分配表,我必須在一排排的希伯來符號之間尋找代表我的那三個英文字母:LEO。我看到了馬克的名字“Mark”,看到了克麗絲蒂娜的名字“Christina”,也看到了達尼埃爾的名字“Daniel”。
但沒有我的名字。我在哪裏?這份名單還有附件嗎?
人們在佈告欄邊的衣帽架上拿自己的遮陽帽和帆布背包。一茬又一茬的人來了又走了,我還在找名字。
霍尼過來了,他就是郵件落款“阿娜特霍尼”裏面的後半部分,他英氣十足,濃密的灰色鬈髮下目光炯炯。他自我介紹說,由於他的英語比較好(意思是能領會我這種東方人可笑的用詞方式),所以我有事可以找他:“里奧,知道你今天的崗位嗎?”
“我還在找呢……”我身邊都站了好幾個人了。
“我來看看,你昨天晚上就應該看好的,”他只簡單地瞥了一眼,“現在你快跟着阿維克多他們去棗椰園,他們在廚房那邊那個門集合,趕快。”
阿維克多,這個名字讓我想起了鱷梨(Avocado),一種非常奇特的食物。我第一次來以色列,就帶回去兩個鱷梨,這是澤埃夫的鄰居,一位長得很像內塔尼亞胡的農民塞給我的見面禮。我愛不釋手,帶着它們通過了本-古里安機場脫內褲級別的安檢,飛了十幾個小時回到家,一直熬到果皮酥軟才把它打開,挖出了許多比榴槤肉還軟的黃色粘稠物,才知道這便是俗稱的牛油果。但凡有人問我滋味如何,我都答“涼的”。
阿維克多開車,戴着頂棒球帽。他大約有五十多歲,胡茬灰白,幾乎謝完了頂,胳膊上有硬糙的鱗片紋路,像從一張舊照片裏走下來的一樣,我是說,像那種長到一定的歲數就不會再老下去的人。我坐在他右手邊,後面是哈慕塔,一個口型很大、說話聲嘎嘎的女孩子,很喜歡用兩隻手拍打膝蓋,只要她一開口,我就知道她跟《列王紀》裏西底家的母親沒什麼血緣關係。他們都問起我來以色列的動機,或者說“使命”,我告訴他們我是讀了這個書,又讀了那個書,以色列的傳奇故事一直在撩撥我躁動的求知欲。
阿維克多開着車進入浩瀚的沙漠裏,這邊是沙漠,那邊也是沙漠。以色列人在沙子裏面開出了很長的公路。內奧·茨馬達名下有一片棗椰園,要在公路上開20分鐘車才能到。我想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法律問題,我問他們,這塊地是怎麼得來的。
阿維克多非常有風度,沒吭聲。哈慕塔在後邊說:“我聽說,像是問政府借的。”我從兩個椅子之間看到她一嚼一嚼的嘴。
“哦,是的。”阿維克多說。
“你們……我們需要上繳多少稅收呢?”耀耀講過,一旦進了農莊就要說“我們”。
“我們的錢不歸我們管,”阿維克多說,“我們的錢是集體的。”
我沒怎麼聽懂。
“我們不太清楚要付多少錢給政府,我知道的是,這塊地的租賃期我們有四十九年。”
“為什麼設這麼奇怪的一個期限?”
其實我應該想得到的。四十九在中國傳統裏也是個有意義的數字,有點威望的鄉紳死了以後,他府上家人要給他停靈七七四十九天,讓肉在入土前爛一爛透,也是因為陰陽兩界溝通不便,最好確保靈魂已經在閻王那兒簽了到才下葬。在猶太教習俗裏,四十九天是從逾越節到七七節之間間隔的日子。逾越節要吃無酵麵包憶苦,而七七節,猶太人要為了感謝上帝賜給他們土地裏的食物而大吃一頓。四十九天裏,虔敬的猶太教徒每天都要念誦《詩篇》第67篇,因為這一篇剛好有49個希伯來單詞。
“這個就是猶太傳統了……啊哈,這裏也是我們的地。”阿維克多指着窗外的一片蓋着白色篷幔的地方。“我們把這塊地租掉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種棉花。呵呵呵,棉花!”他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應該立刻表示出強烈的嫉妒一樣。
棗椰樹站得齊刷刷的,一列又一列,讓我想到以色列境內的茨波利和貝特謝安,這些大型考古遺址裏總有一條通衢幹道,地磚上有粉紅色的花紋,兩邊立着圓柱子。棗椰林裏,滿地都是枯萎墜落的大樹枝,踩上去咯咯的響。“你的鞋穿錯了,”阿維克多說,話音剛落,我的鱷魚鞋前端的窟窿裏就扎到了一根刺刀樣的枯葉。
我們一共有九個人,分成兩組,阿維克多、哈慕塔、我,還有另一個小個子分到了一組。我並不知道要做些什麼。棗椰樹是阿拉伯國家的重要作物,數伊拉克最多,每株樹都甲胄在身,翹起一塊塊棕色的葉板,從樹幹的頂部中心輻射狀地抽出十幾根羽狀複葉,那些葉莖上掛下一捆一捆的果實,無聲地垂着,像雌魚的魚卵。它們種下的時候才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高度,從別處運過來的肥沃土壤滋養着它們,而這些土壤現在也是三十多種稗子的家園。
我們來到一台黃色的履帶式鐵車前,另一些人向另一台車走去。這明明是先進的農業設施,卻一副好像快要病退了的模樣,它的操作中樞一眼是看不到的,因為履帶過於龐大,車體是一圈鐵欄杆組成一個U字形,讓駕駛室顯得特別小而舊,需要靠一個浸過汽油的紙撚發動。阿維克多抓住鐵梁翻身跳進了U圈裏面,我也跟着跳了上去。欄杆周圍繫滿了毛茸茸的麻繩。阿維克多給我一把帶鞘的大鋸。哈慕塔站到了另一頭,小個子直接鑽進駕駛室裏去劃火石了。
車子發動了,先是左右橫走,然後前後走,當一棵棗椰樹向我們慢慢逼近的時候,我們開始緩緩上升。哈慕塔的面孔上出現了享受的神色,是的,高處有一點小風。
“我們的活兒是做不完的,”阿維克多說,手裏撚着一根麻花樣的草繩。我們的上身已經完全扎進茂密的大枝之間了,現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俗稱海棗的果子是怎麼長在樹上的了:在葉腋裏伸出一些扁扁的橘色長莖,長莖上生出幾十根細細的莖杆,杆上有細小的節,每個杆頭上都掛着一顆青青的大棗,捏一捏還是硬的。
“現在開始吧。”
阿維克多把一根橘色的大枝使勁抬起來,椰果東磕西碰,劈劈啪啪地掉下好幾個。“掉了掉了!”我叫道。
“沒有關係,碰一下就掉下來的果實都是不好的!好的果實不會掉。”阿維克多伸手拉了一個棗子過來,連着棗子的細杆子彎成一個優美的弧形,晃了一晃,棗子心領神會地一個斤斗翻了下去。
“這個也是不好的,”阿維克多說,他鬆開手讓那根光禿禿的小莖縮回原位。“你看這些枝都互相纏繞在了一起,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它們分開。”他從腰間抽出根繩子,張嘴一口咬住,抽拉繩頭使得繩子對折,三兩下穿在一根掛了果實的枝上,用力拎住,另一隻手抓住上方的另一根大葉,把這兩根粗壯的東西強扭到一起,不知道是哪一根枝在咯吱吱地叫。“嗨——喲!”果枝抬起來了一點點,棗子又一次發出了嘩嘩的巨響。他的兩隻手在大葉上方麻利地打結。
“看,就是這樣。”阿維克多吐出一口氣,拍拍巴掌。
我們說話這工夫,哈慕塔三兩步地往上攀,已經踩着兩根翹起的大枝的根部,完全站在空中了,好幾根果枝像扇骨一樣在她面前展開,她舒舒服服地背靠樹幹,接二連三地掏出繩子施行結扎術。這個鬆鬆垮垮的女孩兒身手竟如此了得。我沒上過樹,樹上的風光與水裏的一樣新鮮。我想踩着欄杆攀兩下,一看腳下底板磨得溜平的涼鞋……唉,還是算了吧,還是在比較低的位置尋找適合試手的對象吧。我們幾個人全然無語地幹着活。
我們一個接一個踩着一把簡易的人字梯越過了齊腰高的鐵絲網。棗椰樹園邊緣有一塊樹蔭地,擺着幾張蒙着油布的長桌板,一些不知道裝填了什麼東西的黑色麻袋,還有個正圓形的水池,像是怕人覺得水不夠清似的,池子裏面漆成藍色。我們看到,已經有另一些人等候在了這裏,有個穿着綠T恤的人正用一杆長長的火鉗去捅一堆小火,火上擱着一隻漆黑漆黑,好像剛剛從火災裏搶救出來的水壺。
這裏是棗椰園進餐點。人們從板條箱裏拿出大大小小的盤子和刀叉,一個圓桶裏放着洗淨的水杯。早餐是從一個個塑膠箱裏拿出來的:麵包、胡蘿蔔、黃瓜、洋蔥、甜椒、白菜、番茄、甜菜根、嫩得流油的雞蛋……茶端上來了,茶杯裏放着一片碧綠的長葉子,喝起來有股無法描述的味道。世上的大多數味道都是無法描述的:火龍果是什麼味呢?核桃什麼味呢?鵝肝什麼味呢?沒有一本菜譜可以準確傳達菜的味道。中餐菜譜需要對每一道菜的味道做個基本概括,什麼酸甜可口啦,入口爽滑啦,西餐菜譜就比較實在:雞肉土豆火腿沙拉三明治什麼味?雞肉味、土豆味、火腿味、沙拉味和三明治味。
“這茶裏的泡的是啥?”我問。
無語。半晌,坐在我對面的一個姑娘說了聲:
“lemongrass。”
她長得真好看,我不由多看了幾眼,葉芝有個名句:“美貌就像拉緊了的弓”,說的就是這樣的女人。
我點頭,又指着桌上的一條細小的嫩葉:“那麼這個呢?”
“這是巴西利(parsley),”她說,分別點着盤裏其他幾樣東西,“這是芝麻菜(aurogula),這是紫甘藍(redcabbage),這是洋蔥,這是黃瓜。”她一口氣把箭全射了出去,現在沒這麼好看了。
“謝謝……你叫什麼名字呀?”
她莞爾一下:“伊斯迦。”
“哈,是個聖經人物嗎?”
“哦,只是挪亞的後代裏,有一個叫伊斯迦。”
阿維克多用鋸齒小刀把生菜裁成等寬的一條一條,同片狀的番茄放到一起。哈慕塔在倒橄欖油。哦對了,現在餐桌邊可不只有我們在進食,至少還有五百隻蒼蠅列席,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把它們悶死在對折的麵包裏。我切洋蔥時,有兩隻不怕死的蒼蠅一起過來試刀,我用嘴吹,用刀在盤子上狠狠地切出當當的響聲,最後把洋蔥切成味道嗆人的細末,都無法迫使它們退卻。我非常起勁地轟趕桌上這些爬來爬去的傢伙,但很快就發現別人跟我不同。我的肢體語言是“都給我滾!”別人的則是“勞駕借光。”
平靜是農莊裏的最高價值,農莊的人相信修身的第一要務就是輕手輕腳,肢體放鬆,內心像寂寞的深淵,對任何事情都要採取和緩的、溫吞的態度,不宜大驚失色也不宜大喜過望。你小聲地抽泣,自然會有人來過問:跟男朋友拌嘴了?衣服扣子掉了?中午食堂的米飯做酸了?聲音反而會把一些本來很小的事情搞大。吃飯的時候,如果別人的袖子落在自己的沙拉盤裏,你可以捂住嘴,瞪大眼,吃驚地指着對方的袖口,這在農莊還不算是得體的反應,你應該一聲不響地用刀叉把那只袖子拿出去。平靜的習慣使得人人活在一種夢幻的氛圍裏,尤其是內奧.茨馬達的姑娘們,她們缺少普通女子常見的恐懼感。如果你抓一隻鍬甲放在她的肩膀上,並且設法讓他們彼此看見對方,率先尖叫起來的一定是鍬甲。(待續)
作者:雲也退,獨立書評人、譯者。發表文章包括《牢獄化閱讀》《距離之外的閱讀》《我不喜歡“永恆”這個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士兵的日常生活》《移民的身份》《以色列紀行,哪兒都是聖地》等。
題圖:Workerswithabarrel(diptych),NikoPirosmani繪
■回覆“目錄”可獲取往期推送總目錄。
?本公眾號所有圖文資訊均為“今天文學”編輯製作,轉載請注明出處。
﹎﹎﹎﹎﹎﹎﹎﹎﹎﹎﹎﹎﹎﹎﹎﹎﹎﹎
赞赏
人赞赏
兰州可以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哈市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