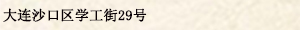一切洒脱,都是对不舍的另一种表达
文初小轨
1
年,我在医科大读医学英语,跟临床医学系的宫琦亲如姐妹。
宫琦有一天突然跑到自修室找到我,非要请我吃一顿全是荤菜的麻辣烫,她说,她摊上事儿了,求我一定要从精神上救救她。
麻辣烫还没吃两口,就看着她紧张兮兮如坐针毡,眼睛里全是急不可耐的催促,我不禁问她:“你劈腿了?”
“……卧槽,小轨,你不能这么绝对而不负责任地定性这么复杂的事儿。”宫琦一听大为不悦,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两眼。
“我没定性啊,我就是问问,你紧张什么,真劈了?”
“嗯……也不算是……就是栾伟不在的这几天……我跟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儿近,但是我没跟他上床啊……”宫琦支支吾吾,开始想办法界定劈腿这件事儿。
“是没,还是没来得及啊?”
“就是……我俩现在是清白的,但是我估摸着也快了……”
“我靠。”
栾伟是宫琦的男朋友,英俊沉稳,已婚,有一个2岁的儿子,在“拥硅为王”的时代,做太阳能发电,这是宫琦讲给我的,但是她从来没见过他的妻子。
大二那一年,栾伟给我们学校赞助了太阳能路灯的电池板,宫琦作为文学社社长兴致勃勃地要去采访他,俩人一来二去聊得十分火热。
后来栾伟每天都在华灯初上时,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等着宫琦从图书馆的方向飞奔而来,如踩长歌,身披三千繁华,心怀朝阳烈焰,一见面俩人就是一如不见隔三秋的拥抱与热吻,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钻进车里,绝尘而去。
宫琦长得虽谈不上惊艳,但清秀白皙,双目盈盈,说话语速总是很慢,任何时候都夹着一本书。第一次看见她时,就觉得她骨子里莫名自带娴静淡雅而目空一切的高冷,大眼睛一翻就能沦陷一个城。
一开始宫琦不知道栾伟有家室,每次约会回来,都面露少女绯红,絮絮叨叨地把我抓过来,逼着我听她一遍遍重温俩人初相识的小暧昧与小青涩。
只是时间一久,俩人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肉体吸引。于是宫琦从此提起栾伟来总是面露羞涩,还要不辞劳苦地用欲说还休的方式渗透我的好奇心,还经常暗示我,男女交欢并不是一件龌龊的事情,来自肉体的确认感是一种神奇的天然反应,来电就必然全身酥软,不来电一道闪电劈死对方也枉然。
宫琦那个时候的追求者多得离谱,吟诗作画弹琴样样出挑,高冷翘课,行踪不定,于是经常被学校里的同学讨论来讨论去。
她班里的同学都说她被社会上的人包养了。
宫琦听说这事儿后十分紧张,从此特别害怕一个人走在路上,她觉得所有的窃窃私语都是对她毫不客气的千夫所指,所以她一下课总是要给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陪她一起走过学校明湖后人潮汹涌的那段路。
三个月后,宫琦跑到我寝室来找我,敲门的时候下手很重,同寝室的姑娘一脸的不乐意,我赶紧扯了件长长的体恤衫往身上一套,就拉着宫琦往图书馆走去。
宫琦一路上用手捂着胸口,问她是否不舒服也不说话,穿过明湖的时候,她浑身一哆嗦,蹲在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出来。
栾伟第一次带宫琦回了家,只是一进门,宫琦就看见了栾伟的婚纱照,那就像是双目失明后迎来的第一缕阳光,扎得眼睛剧疼。
2
万古愁破空而来。
年少的我们,爱胆包天,以为喜欢就是道德,不爱才是过错,完全顾不上爱一场是否会山寒水瘦人仰马翻。
宫琦挣扎着跟我讨论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说自己没有错。
我拍拍她的肩膀,说,人世本就蹉跎,作到最后难免是一场落寞。
宫琦一听,抹了一把未干的眼泪,反手撑了一下身后的台阶,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说,小轨,你这就不地道了,我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痛心的世纪大难题,你竟然还在这说这些有的没的的话,真没劲。
不久之后,宫琦鼓起勇气跟栾伟进行了几次生离死别式的分手尝试,最后都以加倍的思念与不舍偃旗败北而告终,于是在一个大雨纷飞的午后,认了小三的命。
那段时间,宫琦喜欢扎两个麻花大长辫,然后系上薄荷绿小波点的蝴蝶结,安安静静地放在肩膀上,想事儿的时候就拿手指一圈一圈的绕麻花辫。
我看着深感毛骨悚然,觉得这一幕太像一个神经病少女失足前的狂欢,几次三番地阻拦,并在一个周末主动约她去了趟龙口南山,把所有佛祖七零八乱地拜了个遍,下山的时候,我们失魂落魄地像两个被逐出城门的公主,宫琦回头看了一眼烟云高处的南山大佛,突然面露落寞,说,完了,刚才光顾着磕头,忘了跟佛祖说事儿了。
大三上学期,栾伟开始频频南下,在江浙一带忙着搞分布式发电,但是只要一回烟台,就会马不停蹄地奔向宫琦,他们就像失忆的一对青蛙,蹦蹦跳跳地一起翻进了一锅温水中,欢喜着倒计时般的温存,回避着沸腾后不复存在的一往情深。
那段时间,我忙着准备英语专业八级的考试,宫琦开始跟栾伟长期异地。
于是她每天就给自己安排了两件事儿:一件是给我往自修室送饭,她说看到我朝夕努力就觉得人生的希望在冉冉升起;另一件是频频地跑到学校对面的同福客栈里上网,周边的人都带着耳机哗哗地打斗,她就听一首叫《蓝色翅膀》的歌,“一朵花,开在什么地方,它就有什么幻想,告诉太阳,它多期盼,期盼成长,一个人经历多少彷徨,才能长出翅膀,告诉风雨,已经准备,勇敢飞翔”,一直听到自己热泪盈眶,一直听到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宫琦就兴致勃勃地迅速地打开word,写小说,写诗歌。
有时候写给思念,也有时候也写给绝望。
一个中午,她在写一首《最好年华》的诗:
我年少时
满载梦想
却只能远远地望着你幻想
我的身体太年轻
她总是一意孤行
去浪费大把的时间
在一个
不太值得爱的人身上
但这依然
是我最好的年华
刚写完,宫琦就莫名其妙地收到QQ小喇叭的加好友提示,验证消息说,你写得真好。
宫琦感觉后背发凉,于是手忙脚乱地关掉提示框,假装若无其事地往四周一通瞄,推测了半天,到最后也没锁定下来可疑人物,只好坐在椅子上反复撩着叮当作响的大耳环,越想越害怕,索性关掉电脑,撒丫子往学校跑,接着一个男生快步跟上,高声喊着宫琦的名字,说等一下,你等一下啊。
这个男生,就是林远泽。
林远泽是医学影像系的学生,后来宫琦说,她那天刚跑进学校大门,林远泽就在后边穷追不舍,她当时脑子莫名其妙地闪过恐怖片《短柄斧》里的血腥追逐镜头,吓得宫琦把高跟鞋从脚上一把拽下来,疯了一样展开了长达2公里的奔命式逃亡,等她心中的小野兽一脚蹬空反过神来,她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甩开林远泽五百米之远,于是她悻悻地站在樱花树下看清了那张脸,眉毛又黑又长,鼻子挺拔得像个将军,阳光气势汹汹地把他变成了烂漫青春里的一部分。
只是,这对林远泽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3
林远泽每天早上会在2号宿舍楼下等着,一看到宫琦悠悠荡荡地飘下来,他立马神采飞扬地冲上去,把一个甘蓝馅饼和一盒优酸乳塞进宫琦手中,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宫琦你早上到一定得吃饭啊,不能以为自己漂亮就能为所欲为。
宫琦一开始总是把手一甩,说,你别瞎忙活了,我有男朋友。
林远泽一怔,马上支支吾吾地说,有没有男朋友都要吃早饭啊,宫琦一皱眉头,又一甩手,然后就看到馅饼在塑料袋里泛着水珠,带着热气腾腾的希望一下子滚进百花丛中。
第二天,第三天,第不知道多少天,林远泽就像失忆了一样,带着一个馅饼和一盒优酸乳千古不变的搭配立立正正地等在楼下,像一个被设定了等待命令的机器人一样,神采奕奕,不以一切为转移。
直到有一天,宫琦红着眼睛跑下楼,从林远泽手里一把抢过馅饼狼吞虎咽地吃完,冲着优酸乳一皱眉头,说,我从来不喝这种不纯粹的东西,以后给我换成纯牛奶。
那年元旦晚会,宫琦班里同学都带着家属欢聚一堂。宫琦是她班里的文艺委员,她本来想深情脉脉地站在台上给大家来一个诗朗诵,后来她洗脸的时候猛然发现,对长大之后的她来说,静默站立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儿。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先天的尴尬,宫琦决定把我和林远泽请了去当助阵嘉宾,于是当天晚上,我跟林远泽坐在了最后一排等着宫琦的出场。
有人报幕,说到宫琦了。
林远泽在我旁边一下挺直了身子,兴奋地像是一只发现了猎物的土拨鼠。俊朗的侧脸泛着红光,还忍不住拿手肘顶了我一下,说,小轨,小轨,我的宫琦要上台了。
宫琦上台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打通了一个电话,然后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磁性而魅惑的声音,宫琦把麦克对准了手机扬声器,电话那边的栾伟给全场唱了一首《断点》。
很好听,很残忍,那首歌宣告了宫琦确实名花有主,也宣告了,即便是千里之远,也动摇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精神占有的绝对主权。
林远泽没有听完,起身站了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陶醉在歌声中的宫琦,眼睛红红地推门而出,瘦瘦地脊背趴在氤氲的灯光里,缓慢成了一首秋日里无可收获的诗。
宫琦从台上走下来,坐在我身边,歪着头看着我深吸一口气,不知道是在问我还是在自言自语,说:“走了啊?走了啊。”
说完就钻进我怀里嘤嘤地哭了起来,哭完趴在我耳朵上悄悄说,哎,小轨,我发现一件特别操蛋的事儿,他越爱我,我越痛苦。
要命的是,第二天一早,林远泽又手持馅饼与牛奶,静默兀立,任青春马不停蹄,任辜负轻而易举,任陌路天涯两隔。
林远泽有一个周突然回了老家,宫琦从楼上飘荡下来的时候,忍不住就要往芳草萋萋的方向多看两眼,发现空无一人后,竟然一下子欣喜若狂地跳着脚小跑起来,跑着跑着又一下子莫名失落,那一刻手边寒风阵阵,她甚至感受到了具体而巨大的失去。
宫琦开始疯狂地想念栾伟。
有一天,宫琦穿着白大褂从解剖楼出来,她拉着我的手,突然问我,小轨,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我一惊,世间爱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明白的话题,我索性摇头说,不知道。宫琦晃着我的胳膊,说不行,你必须有个答案,错答案也是答案。
我说,爱情就是花间露,草上霜,对错谈不上,笃定一个人,时刻想念他,就算是真爱情。
宫琦咧嘴一笑,说,靠,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啊,我来告诉你吧,爱情就俩字,仰慕。
宫琦对于爱情的定义,就像是一个固执少女心头悬着的一把剪刀,她一厢情愿地规定好了单方面追逐的正确性,也由此付出了惨烈而懵懂的大好青春,直到后来,我去主持了宫琦的婚礼,我又一次问了她什么是爱情。
林远泽不在的那个周,宫琦带着块钱坐着火车千里奔赴,她说,她太想念栾伟了。
林远泽回来的第一天,在楼下迟迟没有等到宫琦,10点多钟的时候,林远泽沉不住气了,惊慌失措地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帮他去看看,怕宫琦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我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宫琦没事儿,你回去吧。
林远泽把我叫下来,他满脸焦虑看着我,手边装馅饼的塑料袋凉透了气,泛着一层奄奄的气息萎缩在白色的苍茫中。
我说,宫琦没事儿,她去无锡了。
林远泽一怔,说,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平安。
我看了他一眼,说,你怎么不自己打给她?
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会陷入一种一厢情愿的担心,会用所有明知不存在的坏可能去贬低自己的智商与自尊,然后傻了吧唧地把这些担心变成想要见到她的卑微借口。
4
宫琦跟栾伟在一起那三年,没有要过栾伟一分钱,她说,她一旦要了,那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小三,如果她只是爱栾伟而不索取,那么她就不构成对别人的婚姻侵犯。
大学里的爱情很艰难,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生活费少则,多则,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松动支扶我们四处浪荡,宫琦每个月都跑一趟无锡,每个月都闹钱荒。
宫琦每天都在学校餐厅解决三餐,对每顿饭的开支进行严格的预算控制,甚至做得出让自己食不果腹的极端行径。她靠近我的时候,时不时地会翻动着辘辘饥肠,突然发出一声响亮而夸张的“咕噜”声。
一向不爱学习的宫琦,甚至为了多筹点路费盘缠,认认真真学习打起了奖学金的注意,只是她日渐憔悴、营养太差,听课听不到十分钟,就精神涣散起来,想栾伟,想无锡,想自己好像永远不可能嫁给栾伟的噬骨悲凉。
不明就里的林远泽跑到自修室,带着七零八乱的小零食往宫琦面前一堆,一本正经地陪着她看书做题,听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
很快,林远泽发现了宫琦的消失规律,每个月3号离开,一周后再回来。
林远泽有一天给了宫琦块,宫琦一脸狐疑地看着他,她深感数额巨大,难免有一些过头的作案嫌疑。
林远泽连忙说,这是他攒的钱,他平时花钱也很省钱,最近他在德州老家的弟弟结了婚,份子钱收了很多,弟弟这个月多给了他一些钱。
这个时候,宫琦才知道,林远泽10岁时便无父无母,上大学的钱,是一个小他4岁的弟弟在老家的一个理发店上班挣来的。
宫琦掐着卷得相当瓷实的钱,想了想,说,那我收下了,短期内还不了,但是我一定会在毕业前还清你。
林远泽在宫琦对面点点头,笑得像是赢了整个人生。
宫琦站起来,扒拉了一下如巍巍高山的课本与复习资料,一翘脚亲了一下林远泽的额头。
林远泽说,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回应,窗外红尘滚滚,一切归于宁静。
后来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宫琦每月离校的一周内,林远泽也会离奇失踪,我忍不住问了宫琦一嘴,她也十分震惊,说,真的假啊,他能去哪儿呢?
宫琦问了林远泽几次,每次林远泽都是支支吾吾,他不擅撒谎,又不肯说实话,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少年在爱情前的缄默与结巴。
直到毕业,学校学生工作处的
当时我在学生会工作,本来是要查实一下我们班是否有拿不到学位证的同学做个通知提示,结果在名单里,我一眼就看到了林远泽的名字。
后来我们才知道,林远泽把学费的一部分扣了下来,偷偷交给了宫琦,林远泽自小清贫,也不好意思朝供着自己读大学的弟弟狮子大开口,更要命的是,在宫琦奔赴无锡的那一周里,林远泽每次都偷偷跟了去,他舍不得买卧铺,于是直勾勾地坐在硬邦邦的座位上随着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去想象一个与他隔了几个车厢远的姑娘,夜色是否太沉,喧嚣是否太浓,她是否还睡得习惯。
林远泽每次到了无锡,为了省钱,都挤在他一个恰巧在无锡打工的发小住处,简陋的出租房里只有一张床,林远泽从发小那借来一条洗得发白的床单,往地上一铺,然后再胡乱垫上几件自己的衣服,直挺挺地在水泥地上度过了他一生中静默无边的陪伴时光。
林远泽掐着宫琦回校日子当天清晨,早早地挤进无锡火车站,看着宫琦恋恋不舍地跟栾伟抱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次又一次,然后耸着肩膀,神情恍惚一抽一抽地上了车,林远泽的心就会一下子沉下去。
火车站鸣笛声夹在在昏暗的灯光中,有人离去,有人转身,一怀愁绪,几年离索,装进火车,呜哇呜哇地咆哮而去,这里像极了如戏人生。林远泽觉得自己这么投入像是一个职业演员,他倒是特想这样寂寂无声地演上一辈子,然后迎来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欢喜结局。
可是现实总是比戏剧精彩。
年,宫琦毕业,干净利落地再次拒绝了林远泽的爱,洒脱转身。
她怀着一腔的爱奔赴无锡,却发现栾伟早已搬家换号。她特别希望栾伟能给她一个好聚好散的说法,比如他不想耽误她,比如他不能抛家弃子,比如他不爱她了,可是栾伟什么都没说,这让宫琦一下恍惚在梦里,怎么也醒不来。
5
毕业后我去了报社。
有一天晚上,宫琦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哭着说她好想杀了栾伟,她根本无法从爱他的诅咒中清醒过来,她觉得他不死她很难好好活。
我问她,林远泽呢?
宫琦楞了一下,喃喃道,对啊,林远泽呢?他好久没联系我了。
我们自此失去了林远泽的下落。
我当时莫名其妙的坚信,林远泽爱得这么坚韧,怎么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这样放下了宫琦。
1年后,宫琦复读一年考上了青岛大学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医院成了一名妇科大夫。
毕业后的几年内,宫琦遇人无数,她怀着对爱情的仰慕之心兜兜转转,谈了几次恋爱,始终也没什么结果。
宫琦说,人这一辈子,真爱也就这一次,你一下子倾尽所有,接下来只能剩下漫长的消耗与爱无所爱。
年3月中旬,我收到了宫琦的请帖,她说新郎是一个老中医,婚宴设在北京,我看了下日子,刚好那几天我约了一个出版公司送合同,于是从大理长路漫漫地飞过去。
宫琦在婚礼上还给我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给她做婚礼主持。
4月15号,婚礼如期进行,宫琦穿了一件宫廷蕾丝范儿的长裙,美美地笑在酒店灯光的三千繁华中,她拉着我挨桌介绍,这一桌是骨科的,那一桌是妇科的,东北角那桌呢,是产科的……整个婚宴现场的格局,医院各个科室大夫的民族大融合。
然后一个转身,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叫到了跟前,笑嘻嘻地说,来来来,小轨,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一位出色的老中医。
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老中医羞涩地伸出手来,彬彬有礼地说,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以前经常听宫琦说起你来,我媳妇一天天净是傻乐。
婚礼上,我看着笑靥如花的宫琦,内心莫名伤感,我举着话筒问她,宫琦,你觉得什么是爱情?
宫琦怔住了,三秒之后,她说,爱人在怀,阳光在手。
我忍不住大笑,说,不再是仰慕了吗?
宫琦突然把手放在鼻子上,长吁一口气,说,一个人男人再好,你再仰慕他,可是他又不肯对你好,那他只能属于全世界啊,跟你的爱情毛关系都没有啊。
我脑子一抽,这些年的沧桑巨变杂糅着万千疑问变成一个极其幼稚而无趣的问题,我说,那你喜欢老中医什么?
“我喜欢他很男人,有责任心啊。”说完宫琦就朝着我挤眼睛,唯恐我再问下去就给她砸了场子,乐得我赶紧谢过全球顶尖医疗阵容超强战队的来宾后,走下台去。
一抬头突然看到门口一个萧瑟而熟悉的影子,那么匆忙地转身就要离去,决绝地就像是走错了房间。
我赶紧追了过去,相比于若干年前那个一意孤行不问因果的傻小子,林远泽现在看上去何其洒脱,他身上貌似有了一种宫琦多年前迷恋的仰慕品质。
晚上林远泽带我去樱花屋日本料理吃饭,我问他怎么不进去,至少假装说一句新婚快乐。
林远泽苦笑一声说,我说不出口。
毕业之后,林远泽因为欠学费没能拿到学位证,一时间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医院对本科学历的医学生来说几乎就等于百分百不可能,况且林远泽连个正经学位证都没拿到,所以只能在周边找了个鸡零狗碎地活打工把欠下的学费交上,拿到学位证后已经是毕业后3个月的事儿了。
他想去找宫琦,但看到自己一身破落,居无定所,连个工作都没有,一种巨大的无力与自卑感在天地间升腾,他一直都知道卑微而一厢情愿的爱从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心里默默地说了一万遍“宫琦你一定要等我”,后来一狠心,就去了上海。
林远泽现医院一个科室的主任,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不算配得上宫琦,只是一直用直觉支持着自个再等等,这一等就是6年。
滑稽地是,林远泽在一次医学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老中医,两个人一交谈,发现竟然同在烟台上过学,深感三生有缘,各种相见欢,各种恨识晚,此后他便收到了老中医的新婚请帖,看着请帖上新娘的名字,他觉得自己那一刻行走在云端然后一脚蹬空,这样的坠落好像是一种彻底的失去。
林远泽说,推开酒店的那一刻,他吓得没敢睁开眼睛,他默念三声,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一睁眼就看见宫琦笑靥如花地站在熙熙攘攘地恭贺人群中,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吓得一哆嗦。
他突然觉得手里没有馅饼和牛奶,这样的人生,不是宫琦喜欢的纯粹。
第二天一早,林远泽送我去机场,他说他这下甘心了,说完便扭过头去,我看到凌晨四点的雨水在他脸上飘落。
我问他当初消失得那么洒脱,是不是因为还是恨了她。
林远泽一边后退着一边朝着我振臂高挥,哽咽着说,当初洒脱,只是因为不舍。恨只恨,在最美好的年华爱了她。
突然想起宫琦那首诗:年少时,我们的身体太年轻,所以总是一意孤行,把大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不太值得爱的人身上。
但这依然,是我最好的年华。
初小轨,87年水瓶女一枚,山东人,品牌策划人,互联网运营人,广告人,网络小说作者。 ?点击菜单上的“美文调频”选项收听有声电台,隔天更新。也可以在荔枝fm、喜马拉雅及podcaat搜索美文调频进行订阅。急性白癜风北京那个医院看白癜风看的好
| |